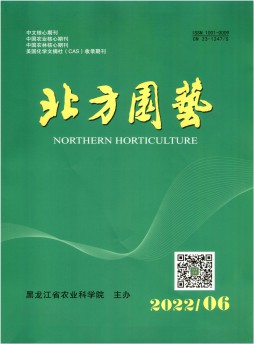北方旱區(qū)農(nóng)業(yè)水利的生態(tài)化轉(zhuǎn)型范文
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(zhǔn)備了北方旱區(qū)農(nóng)業(yè)水利的生態(tài)化轉(zhuǎn)型參考范文,愿這些范文能點(diǎn)燃您思維的火花,激發(fā)您的寫作靈感。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。

一、傳統(tǒng)水利社會(huì)研究
在農(nóng)村公共品供給研究領(lǐng)域,農(nóng)村水利因其獨(dú)特價(jià)值,占據(jù)了十分重要的地位。水利占據(jù)著至關(guān)重要的地位,維系著農(nóng)業(yè)社會(huì)的命脈。從社會(huì)科學(xué)的視角看,“水利與社會(huì)之間的關(guān)系,先要確認(rèn)這種流動(dòng)的物質(zhì)是農(nóng)業(yè)社會(huì)的核心資源”[1],“水利對(duì)于中國(guó)社會(huì)的理解,有著至關(guān)重要的意義”。
社會(huì)史和政治學(xué)領(lǐng)域?qū)λ芯砍晒^為突出。冷戰(zhàn)時(shí)期,魏特夫根據(jù)文獻(xiàn)資料撰寫而成的《東方專制主義》,將東方政治制度與水利系統(tǒng)進(jìn)行了因果分析,雖然其結(jié)論受到了很多詬病,但是,他將水利與政治聯(lián)系在一起進(jìn)行分析的思路卻與水利本身的運(yùn)行規(guī)律暗合,在魏特夫之后的學(xué)者大多也遵循其研究路徑,將對(duì)水利探討與政治制度進(jìn)行一番聯(lián)系。
黃宗智探討了華北旱作地區(qū)的農(nóng)業(yè)水利與地方政治經(jīng)濟(jì)結(jié)構(gòu)的關(guān)系,前后撰寫了兩篇著作———《華北的小農(nóng)經(jīng)濟(jì)與社會(huì)變遷》和《長(zhǎng)江三角洲小農(nóng)家庭與鄉(xiāng)村發(fā)展》,通過歷史地域的縱橫比較,黃宗智認(rèn)為,“兩者也許可以視為同一生態(tài)系統(tǒng)里互相關(guān)聯(lián)的兩個(gè)部分,現(xiàn)出自然環(huán)境與社會(huì)結(jié)構(gòu)之間的相互作用”[2]。在華北平原,水利工程主要由龐大的防洪工程和微小的水井構(gòu)成,“由國(guó)家建造和維修的大型防洪工程與由個(gè)別農(nóng)戶挖掘和擁有的小型灌溉井之間的對(duì)比,足以顯示政治經(jīng)濟(jì)結(jié)構(gòu)中的一個(gè)強(qiáng)烈對(duì)照,即龐大的國(guó)家機(jī)器與分散的小農(nóng)經(jīng)濟(jì)之間的懸殊差別”[3],而“在長(zhǎng)江和珠江三角洲地區(qū),典型的治水工程的規(guī)模,介于華北的大型堤壩和小水井之間。三角洲地區(qū)有渠道排灌系統(tǒng)貫通江湖。湖邊、低地四周常有堤圩,為防洪、圍田之用。這類水利工程需要數(shù)十、數(shù)百乃至數(shù)千的勞力,是一個(gè)宗族的組織所可能應(yīng)付的”[4]。
不同的水利系統(tǒng)決定性地對(duì)社會(huì)和經(jīng)濟(jì)結(jié)構(gòu)形態(tài)產(chǎn)生影響的這種觀點(diǎn),在水利史學(xué)的研究中也多有體現(xiàn)。冀朝鼎的《中國(guó)歷史上的基本經(jīng)濟(jì)區(qū)與水利事業(yè)的發(fā)展》一書通過水利來對(duì)中國(guó)歷史上的基本經(jīng)濟(jì)區(qū)域變遷進(jìn)行闡釋。而人類學(xué)著作則更加強(qiáng)調(diào)水利社會(huì)的文化網(wǎng)絡(luò),力圖達(dá)成水利管理目標(biāo)的社會(huì)如何憑借宗教、宗族、娛樂等文化手段進(jìn)行整合。在人類學(xué)視野中,水利賦予著農(nóng)業(yè)社會(huì)多方面的社會(huì)與文化特征,主導(dǎo)著農(nóng)業(yè)社會(huì)的組織規(guī)則,運(yùn)行邏輯。無論是宗族與國(guó)家權(quán)力、權(quán)力與控制、宗教信仰,甚至道德觀、通婚圈、文化網(wǎng)絡(luò)等等都可以透過水利研究得其個(gè)中三昧。弗里德曼在中國(guó)東南的宗族組織》一書中,對(duì)中國(guó)邊陲稻作農(nóng)業(yè)社區(qū)的水利系統(tǒng)和宗族組織進(jìn)行研究,得出宗族組織與水利社會(huì)的關(guān)聯(lián)性假設(shè),他說:“水稻的種植是使繼嗣的地方社區(qū)易于將自己建立成為一個(gè)大的社區(qū)的條件之一”[5]。弗里德曼的假說受到來自他弟子巴博德的挑戰(zhàn),巴博德感興趣的問題是“一個(gè)社區(qū)的水利系統(tǒng)怎樣影響到該地區(qū)的社會(huì)文化模式,例如,沖突與合作、勞力的供給和需求以及家庭的規(guī)模和結(jié)構(gòu)”,他通過研究力圖表明“地方不同的灌溉模式能導(dǎo)致重要的社會(huì)文化適應(yīng)和變遷”[6]。
格爾茲則在對(duì)巴厘水利社會(huì)的研究中,剖析了灌溉社會(huì)的政治邏輯,通過灌溉會(huì)社來透視巴厘社會(huì)組織、社會(huì)分層以及“國(guó)家與社會(huì)”之間的關(guān)系。為東方社會(huì)水利研究提供了一個(gè)社會(huì)上逐級(jí)分層、空間上散布四方、行政上非集權(quán)化、道德上實(shí)行強(qiáng)制性的儀式義務(wù)團(tuán)體[7]。費(fèi)孝通從對(duì)開弦弓村灌溉排水的觀察中,敏銳地意識(shí)到水利與農(nóng)民合作的問題。“水的調(diào)解是需要合作進(jìn)行的。在灌溉過程中戶的成員,包括女人和孩子都在同一水車上勞動(dòng)。在排水時(shí)必須把一瑾地里的水從公共水溝里排出去。在同一瑾地里勞動(dòng)的人是共命運(yùn)的。因此便出現(xiàn)了一個(gè)很好地組織起來的集體排水系統(tǒng)”[8]。
正如姚漢源先生所期待的那樣,水利作為社會(huì)發(fā)展的一部分,應(yīng)該有一個(gè)從政治、經(jīng)濟(jì)、社會(huì)等多角度探討水利及其互動(dòng)關(guān)系的研究局面[9]。水利社會(huì)就是“以水利為中心延伸出來的區(qū)域性社會(huì)關(guān)系體系”。所以,挖掘當(dāng)前中國(guó)普遍出現(xiàn)的農(nóng)業(yè)社會(huì)水利缺失的社會(huì)肌理,縱深地探究維系水利延續(xù)的社會(huì)關(guān)系網(wǎng)絡(luò)的斷緒,才能重新將當(dāng)代水利放置于一個(gè)可能再生并可以維護(hù)生態(tài)良性發(fā)展的社會(huì)網(wǎng)絡(luò)之中。
1949年之后,國(guó)家通過對(duì)農(nóng)民進(jìn)行了強(qiáng)有力的組織,借助資源調(diào)配優(yōu)勢(shì),農(nóng)田水利設(shè)施發(fā)展很快。1980年代中后期,由于國(guó)家力量逐漸退出農(nóng)村公共產(chǎn)品供給領(lǐng)域,水利變成市場(chǎng)化、家庭化,農(nóng)村水利社會(huì)出現(xiàn)了許多現(xiàn)實(shí)性的問題,水利社會(huì)的應(yīng)用性研究成為三農(nóng)研究領(lǐng)域的重要組成部分。“鄉(xiāng)村水利作為公共品,具有私人提供不經(jīng)濟(jì),只能由一些農(nóng)戶聯(lián)合起來提供的特征”[10]。水利利用管理的討論牽涉到多層次多方面的問題,如國(guó)家與社會(huì),政府與民間組織、私人市場(chǎng)化與重新“集體化”等等。
由于水利討論牽涉國(guó)家、社會(huì)關(guān)系最多。主張通過市場(chǎng)化辦法來解決微觀水利供給問題的學(xué)者,多主張弱化政府權(quán)力,發(fā)揮市場(chǎng)化所帶來的公正與效率[11]。主張強(qiáng)社會(huì)弱國(guó)家模式的學(xué)者借鑒國(guó)外經(jīng)驗(yàn),設(shè)計(jì)出農(nóng)戶用水協(xié)會(huì)組織這樣的自治性質(zhì)的管理機(jī)構(gòu),其具體結(jié)構(gòu)是,由農(nóng)戶以村民小組或村為單位組織用水協(xié)會(huì),由農(nóng)戶選舉產(chǎn)生用水協(xié)會(huì)會(huì)長(zhǎng),由會(huì)長(zhǎng)負(fù)責(zé)收取水費(fèi)并組織農(nóng)戶灌溉[12]。賀雪峰、羅興佐則通過調(diào)查指出,農(nóng)村稅費(fèi)改革后,農(nóng)村普遍存在公共品供給不足的問題,當(dāng)前農(nóng)村水利遇到的最大障礙是農(nóng)民“原子化”,“缺乏社會(huì)記憶與缺乏社會(huì)分層”的社區(qū),無法組織化地利用水利資源,由于合作成本高,國(guó)家提供的低成本水利資源無法與微觀的農(nóng)業(yè)用水戶之間掛鉤。羅興佐、賀雪峰認(rèn)為,在水利運(yùn)作的管理上,由于宗族和宗教等傳統(tǒng)力量消失,導(dǎo)致農(nóng)村社區(qū)在公共品管理上缺乏道德監(jiān)督,搭便車現(xiàn)象嚴(yán)重也是阻礙農(nóng)田水利組織化的障礙。
綜上,我們似乎發(fā)現(xiàn),學(xué)者們似乎總是通過對(duì)某個(gè)或某幾個(gè)水利社會(huì)的研究來構(gòu)建一個(gè)宏大的闡釋,其實(shí),通過對(duì)這些研究成果的綜述,我恰恰要說明,“在不同的歷史時(shí)期,不同的區(qū)域,水利具有的意義,可能因此有所不同。這些不同能導(dǎo)致什么樣的社會(huì)和文化地區(qū)性差異?這些文化和地區(qū)性差異,與中國(guó)歷史中國(guó)家與社會(huì)關(guān)系的地區(qū)性差異之間,又有什么聯(lián)系?若說傳統(tǒng)中國(guó)社會(huì)圍繞著‘水’而形成這些復(fù)雜關(guān)系,那么,這些關(guān)系是否對(duì)于我們今日的水利和社會(huì)起著同樣重要的影響?問題等待研究”[13]。本文研究建立在我國(guó)北方某一旱地農(nóng)村社區(qū)的調(diào)查基礎(chǔ)上,通過跨時(shí)空的比較,來將這一地區(qū)面臨的水利困境鎖定在特定的時(shí)空條件下,在探討水利社會(huì)常用的“自上而下”或“自下而上”的國(guó)家/社會(huì)研究框架之外,引入生態(tài)緯度,為水利社會(huì)研究提供一個(gè)新的研究視角。
在生態(tài)十分脆弱的北方社區(qū),研究水利的視角既不能局限于傳統(tǒng)水利社會(huì)的思路中,為水利不興而哀嘆,也不能簡(jiǎn)單地用國(guó)家/社會(huì)的研究框架,將水利問題的解決寄托在“自上而下”或“自下而上”,前者多眼光鎖定傳統(tǒng)的水利自治管理模式,期望通過模擬傳統(tǒng)水利社會(huì)中的宗族、宗教、娛樂等組織和道德規(guī)范來挽回當(dāng)今水利社會(huì)的頹勢(shì);后者則陷入自由主義和國(guó)家主義的意識(shí)形態(tài)爭(zhēng)論中,對(duì)認(rèn)識(shí)問題于事無補(bǔ),我認(rèn)為這些觀點(diǎn)都沒有真正切中水利問題的關(guān)鍵。末級(jí)水利與地方性社會(huì)邏輯關(guān)聯(lián)最近,遇到的問題也最有可能千差萬別,無論是借鑒傳統(tǒng)模式,還是討論國(guó)家與市場(chǎng)的關(guān)系,都要根據(jù)實(shí)際出發(fā),必要的時(shí)候轉(zhuǎn)變思路,才是找到解鎖之鑰的良策。
二、歷史脈絡(luò)中的水利社會(huì)
我調(diào)查的地點(diǎn)福鎮(zhèn)位于內(nèi)蒙古赤峰市西部偏北,距離市區(qū)行車要3個(gè)半小時(shí)。從赤峰進(jìn)入大廟沿途有老哈河的支流,沿河而居的田地里可以種植水稻。當(dāng)時(shí)我下去的時(shí)候,正值春天,插秧時(shí)節(jié),看農(nóng)民挑著嫩綠的秧苗下田插秧,頓覺有塞外江南之感。快到福鎮(zhèn),老哈河支流不再北流,陡然南下,山峰多了起來,地表水流則稀見,水田也絕不再見了。我所在的營(yíng)子位于大廟北20分鐘路程的地方,整個(gè)營(yíng)子被一群群不高的山峰合圍,山峰的南北隘口被一條來自外界的路穿過,這條路東南通赤峰,西北聯(lián)結(jié)著娘娘廟、東山等等大大小小的鄉(xiāng)鎮(zhèn)、直到蒙古族比較多的巴林左、巴林右旗等地。路也穿行于村子,路是泥土路面,允許兩輛面包車并行通過的寬度,村民沿路蓋房,村子形成了狹長(zhǎng)的一條,分東、西兩部分。營(yíng)子周圍是村里的耕地,平地幾乎都被開墾了,山坡上也部分地開墾出了一些農(nóng)用地。近幾年由于封山造林,不讓在山坡上開墾耕地,由于耕地稀缺,還是有人偷偷地開墾,春天要是降了雨,就趕緊播種些谷子等抗旱的作物,要是一個(gè)春天都沒有降雨也就荒廢不種了。
營(yíng)子當(dāng)中有一棵大槐樹,以它為界整個(gè)營(yíng)子被分為南北兩個(gè)部分,南邊是3組、4組,北邊是5組、6組,我住在6組是位于營(yíng)子的最北頭。不少老人說,這個(gè)老槐樹有些年頭了。以前槐樹旁邊有口井,現(xiàn)在家家都打了機(jī)井之后井也廢了,被添平了。干旱少雨困擾著當(dāng)?shù)剞r(nóng)民,由于長(zhǎng)年機(jī)井灌溉,造成地下水位下降。每當(dāng)春耕灌溉水量需求大的時(shí)候,地頭的機(jī)井總是不停地工作,地下水位突降,幾乎家家的井都宣告干涸,人們只得治井來維持生活用水的供應(yīng),地下水位則繼續(xù)下降,形成惡性循環(huán),每年因?yàn)榇焊墓喔?地下水的水位都要突降4米左右,我真為生活在這里的人們擔(dān)心,一旦水沒有了,該怎么辦。這個(gè)春天,我和營(yíng)子里所有人都等待著一場(chǎng)好雨,廟會(huì)開始的頭一個(gè)星期,終于下了一場(chǎng)雨,整整下了一天的大雨使旱情終于得到了緩解。當(dāng)?shù)赜幸粋€(gè)小型的水利設(shè)施,叫紅衛(wèi)渠,曾經(jīng)從老哈河支流引水灌溉,雨水充沛時(shí),其水量可以形成一條寬達(dá)三十幾米的河流。這個(gè)涂抹著革命色彩的渠,修建于上個(gè)世紀(jì)60年代,如今50歲往上的老人還記得當(dāng)時(shí)父輩們是如何為之出力流汗的。和中國(guó)的其他許許多多農(nóng)村一樣,“自1980年代中后期以來,該地區(qū)對(duì)水利建設(shè)重視程度和投入力度大大削弱,甚至于一些現(xiàn)有的水利設(shè)施的維護(hù)和保養(yǎng)都已經(jīng)得不到保證,水利設(shè)施毀損和新的水利困難接踵而至”[14]。紅衛(wèi)渠也在七年前徹底被廢棄不用了。
一眼眼機(jī)井密密麻麻地遍布整個(gè)村莊,村子南邊有幾家廢棄的院子———因?yàn)樗幌陆?井水枯竭,而搬遷到了北邊,村子在悄無聲息地向北部蔓延,荒蕪的南邊則呈現(xiàn)了沙化的跡象。莊稼長(zhǎng)起來了,其代價(jià)是大量地開采地下水,水位嚴(yán)重下降,天然植被遭到毀滅性地破壞,在村子里,除了幾株樹齡較長(zhǎng)楊樹還依然吐綠,幾乎寸草不生。福鎮(zhèn)基層水利陷入了多重困境,如政府公共資金缺位;水利設(shè)施的管理和提供基本實(shí)行承包制,導(dǎo)致水利設(shè)施建設(shè)投入不足,水資源利用出現(xiàn)嚴(yán)重的短視效應(yīng);農(nóng)戶組織無序,搭便車現(xiàn)象嚴(yán)重。就當(dāng)?shù)氐纳鷳B(tài)狀況看,用不了多久,打井取水的做法無異于飲鴆止渴。福鎮(zhèn)的水利困境應(yīng)該是全國(guó)農(nóng)業(yè)區(qū)水利困境的一個(gè)縮影,在全國(guó)許多地方,都存在因以上因素而造成的公共水利設(shè)施癱瘓,分散利用水資源浪費(fèi)的情況。“利”作為水存在于農(nóng)業(yè)社會(huì)之本,水利總是被視為一筆重要的財(cái)富。無論對(duì)于普通農(nóng)戶,還是康莊之家,水利關(guān)乎土地收益。作為農(nóng)業(yè)社會(huì)的利之所在,就維系在水的上面①。
水利可以使莊稼收成,轉(zhuǎn)化為食物和貨幣以外,水利作為財(cái)富有時(shí)候表現(xiàn)得更為直接。1949年以前,地方社會(huì)水利管理系統(tǒng)將水作為可以買賣的資源進(jìn)行分派并實(shí)施貨幣化操作。事實(shí)上,水是可以買賣的資源的這種觀念,一直植根于這個(gè)水利管理系統(tǒng)中。山西的《晉祠志》記載了這個(gè)方面的資料。“……訊之北河渠長(zhǎng)據(jù)稱:‘晉祠用水自古及今有例無程,每年先澆晉祠無程地,然后?及各村有程地”等語,據(jù)此則九口稻地原在應(yīng)澆之例矣。王杰士居住王郭村,為南河四村渠長(zhǎng)一十六年,越界強(qiáng)霸九口稻地水例,無錢不許灌澆,謂無例地也’”[15]。以及作為輪流供水體系的一個(gè)部分,渠長(zhǎng)們向用水的村民收費(fèi),同時(shí)出售剩余的水。截至1916年,在數(shù)百年的時(shí)間內(nèi),花塔渠長(zhǎng)一直按照每畝26文錢的比例收取費(fèi)用,而所有用北河水灌溉的土地,則每畝增收50分文錢的費(fèi)用[16]。這也是花塔渠長(zhǎng)在夏季輪流灌溉結(jié)束后售水的標(biāo)準(zhǔn)價(jià)格。
甚至據(jù)傳,當(dāng)?shù)赜袐D女出嫁,竟然帶走了水利管理權(quán),“傳言:舊名鄧家河,系東莊營(yíng)鄧姓經(jīng)營(yíng)河事。不知何年鄧家有火需婦再醮,將《河冊(cè)》隨至北大寺村武家,遂憑《河冊(cè)》自為渠長(zhǎng),東莊營(yíng)人爭(zhēng)之不得”[17]。婦女可以帶走的財(cái)產(chǎn)中竟然包括了水利管理權(quán),坐水利來漁利,確實(shí)可見,在農(nóng)業(yè)社會(huì),水利作為重要財(cái)富的事實(shí)。對(duì)這樣的情況,劉大鵬在《晉祠志》如此評(píng)價(jià):“灌溉麥田已畢,謂公事完竣,即許渠甲售水魚利,此大弊也。夫溉麥已畢,仍系兩程水,此水為村中公共之水,非渠甲可擅為己之水,胡為任其售耶?同為村人而有錢者澆,無錢者即莫能灌,事不均平,一至于此,殊可扼腕”[18]。對(duì)于農(nóng)業(yè)社會(huì)來說,水利的興敗關(guān)乎一方土地的富庶與否,明清時(shí)期,山西洪山泉水域介休水利主宰了當(dāng)?shù)亟?jīng)濟(jì)的興衰。水利興時(shí),洪山泉域成為明清時(shí)代直至解放初期介休最為繁榮富庶的地區(qū)。到了“源涸難繼”時(shí),當(dāng)?shù)氐慕?jīng)濟(jì)也受到了致命的打擊[19]。
任何財(cái)富都需要血來祭祀,水利也不例外,越是農(nóng)業(yè)發(fā)達(dá)的地區(qū),對(duì)水的要求越強(qiáng)烈,常常會(huì)演化為暴力沖突。水利社會(huì)研究的學(xué)者大多會(huì)注意到,械斗貫穿于地方社會(huì)水利史的幾條主線中,所謂“械斗之動(dòng),動(dòng)于利也”[20]。劉興唐注意到泉州地方志記載的帝國(guó)法令:“近聞?wù)摹⑷粠?百姓嘯傲好斗。強(qiáng)宗大族,仗勢(shì)多人眾,欺壓弱宗小族。……”械斗起因一是田畝之爭(zhēng),其次就是水利之爭(zhēng)了,而且正是由于水具有流動(dòng)性和季節(jié)性,不易看守,所以更成為械斗的導(dǎo)火索。“世仇的操縱簡(jiǎn)化成一個(gè)體系,相互仇視的家庭時(shí)刻準(zhǔn)備攜帶劍器和棍棒參加這些并不總是不流血的爭(zhēng)吵。在這些地方,敵對(duì)的雙方相距甚近,從事著他們的勞作和收獲每一方都生活在對(duì)方的眼皮底下,不時(shí)地出現(xiàn)喚起心中仇恨的機(jī)會(huì)。假如一方在仇家的小塊田地扒開缺口,將水放入自家的田地……兩個(gè)村落的所有村民都卷入沖突之中”[21]。
如果說水利之利在于其財(cái)富性,那么水利之水就在于其公共性。在中國(guó)的各個(gè)地方,人們對(duì)水利管理遵循一個(gè)倫理原則,即公正。人們對(duì)這一倫理觀念的價(jià)值表述是這樣的:
問:植物為什么能生長(zhǎng)?
答:因?yàn)橛型恋睾陀晁?/p>
問:為什么?
答:因?yàn)樗鼈儚耐梁退畠?nèi)獲得了能量。
問:雨水有能量嗎?
答:有。
問:誰賦予雨水以能量?
答:雨水是由玉帝的下屬———龍王創(chuàng)造的。雨水中含有龍王的力量。
問:為什么龍王要下雨?
答:水是萬物之源,沒有它人們便無法生存,龍王下雨以救人類。
問:當(dāng)雨水尚未落地之時(shí),它歸誰所有?
答:盡管龍王按玉帝的命令行事,但雨水為龍王創(chuàng)造,所以歸龍王所有。
問:雨水落地之后它是否還歸龍王所有?
答:土、水為公(歸大家所有)。[22]
對(duì)水利分配的公正原則的追求,促使人們?cè)诘胤焦餐w為基礎(chǔ)的單位,進(jìn)行組織化的管理,在中國(guó)東南邊陲的漢人社會(huì),出于保護(hù)財(cái)富的需要形成了各種防御性組織,如弗里德曼認(rèn)為,在該地區(qū)宗族存在的原因是由四個(gè)變量造成的,前兩個(gè)重要變量為:水稻栽種需要水利的灌溉,稻作農(nóng)業(yè)導(dǎo)致財(cái)富的剩余。而在中國(guó)北方地區(qū),圍繞著對(duì)水利的分配、保護(hù)和管理,則形成了以追求公正為目的的分層化社會(huì)管理機(jī)制[23]。“與中國(guó)南方及其他區(qū)域不同,宗族勢(shì)力、鄉(xiāng)紳集團(tuán)在晉水流域水資源的爭(zhēng)奪和祭祀活動(dòng)中并沒有顯現(xiàn)出特殊的角色功能,而各村莊推舉出的渠甲卻有著無可替代的、舉足輕重的地位和作用。重要的是,渠甲并不是宗族和鄉(xiāng)紳的代表,相反則是某一村莊利益公共體的代表。……以村莊為共同利益的公共團(tuán)體,才是晉水流域多村莊水利祭典中最重要的實(shí)際角色”[24]。地方志中對(duì)水利管理的記載,充分說明了人們是如何利用組織力量來對(duì)利益進(jìn)行巧妙配置,以實(shí)現(xiàn)水利分配倫理中的公正原則。“山西地方使水溉田,每渠大都分別有長(zhǎng)期固定之秩序,也有因時(shí)而定之序次。如此秩序或次序,時(shí)在從前特定的社會(huì)形勢(shì)和時(shí)代背景下產(chǎn)生的,是鄉(xiāng)村大眾利益的需要,是圍繞著公平合理的精神制定的,它基本反應(yīng)了清代三晉農(nóng)民的意愿,即民眾主張有合理的灌溉秩序”[25]。
清代,三晉地區(qū)的民間社會(huì)逐步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水利管理系統(tǒng),即主要是由擁有水利并列入渠冊(cè)的農(nóng)戶來進(jìn)行自組織管理。在臨汾、趙城、洪洞地方,每個(gè)有相應(yīng)規(guī)模的引水渠上都立有渠冊(cè),規(guī)定“水例”條款。遵照渠冊(cè)規(guī)定,于每條渠道上設(shè)立渠長(zhǎng),具體操辦河渠公務(wù),下設(shè)水甲若干名,協(xié)助渠長(zhǎng)工作,渠長(zhǎng)和水甲皆由民選,按年輪換,屬于一種差役。在普潤(rùn)渠上,各村夫頭(由水田的農(nóng)戶代表,也由公選)人等限二月初一日俱至某村某廟聚集,公舉有德行之長(zhǎng)為渠長(zhǎng),總管夫役,每年輪流更替。每村仍舉甲頭(溝頭)二人,巡水三人,分管該村渠事。一般渠上的組織機(jī)構(gòu)有兩個(gè)層次,渠長(zhǎng)和水甲。選舉渠長(zhǎng)和水甲的時(shí)間一般在正月初至二月初,而各渠還有特別的固定時(shí)日。渠長(zhǎng)、水甲有候選人,候選人稱“夫頭”。先由百姓選出,然后再由夫頭集會(huì),選出渠長(zhǎng)和水甲。……各渠的渠長(zhǎng)統(tǒng)籌渠務(wù),預(yù)先布置水利活動(dòng),應(yīng)用物料要制備齊全,及時(shí)召集水甲及夫頭集議渠事,安排河道、渠堰工程。水甲時(shí)常巡查渠道,看守渠堤工程,并巡查情況匯報(bào)渠長(zhǎng)。
每年開春,土地解凍時(shí),渠長(zhǎng)要通過水甲或溝頭組織水戶挑浚河渠。人員和時(shí)間規(guī)定很嚴(yán)密,如“每夫(幾畝或幾十畝定為一夫)每日撥夫二名,限十日內(nèi)掏完。”“掏渠工竣,渠長(zhǎng)擇日傳各夫興工堵堰治水,引水如渠,挨次灌溉,不得有誤,如此而已,有誤科罰。”渠長(zhǎng)及溝頭撥派夫役,組織農(nóng)戶進(jìn)行渠務(wù)活動(dòng),是根據(jù)“夫薄”分配勞力的。“夫薄”是按渠冊(cè)所載條款訂立的。各渠先編夫立冊(cè),然后再派役興工。編夫的辦法是按土地的數(shù)額來折算。受益多則付出人力也多,反之亦然。無論開渠還是筑堤打堰,所需經(jīng)費(fèi)皆由渠長(zhǎng)自籌。……通常情況下,俱為用水農(nóng)戶集資自興。有時(shí)農(nóng)民自行組織,有時(shí)官府勸諭發(fā)起或督率組織。各渠所在村莊,除了均出夫役外,渠道所需和備用工程物料、雇募用款,一列在村民中攤派。河渠堤壩經(jīng)費(fèi),除了按畝均攤外,有時(shí)一些官吏、紳士也捐獻(xiàn)錢物。
各渠所屬村莊之各段水田澆灌時(shí),一般皆要輪使牌照,稱為水牌。使水時(shí)將水牌立于界區(qū),無牌不能澆。如麗澤渠規(guī)定“本渠上起置木牌一面,長(zhǎng)二尺,厚二寸,闊一尺。木印一顆,長(zhǎng)八寸,厚五寸。渠水流到時(shí)刻,并行水牌、水印、水歷,預(yù)先交付。”有的渠道是用“溝棍”代替水牌,性質(zhì)相同[26]。②
以上資料翔實(shí)地記述了傳統(tǒng)社會(huì)地方社會(huì)水利資源管理狀態(tài)。首先,地方社會(huì)是通過組織行為來進(jìn)行水利資源的管理,并且通過管理水利強(qiáng)化了地方社會(huì)的組織性;其次,水利組織具備了良好的社會(huì)分層,社區(qū)精英承擔(dān)了推動(dòng)組織運(yùn)行的責(zé)任,這些被民間社會(huì)推舉出來的精英,同時(shí)也被官方賦予一定的權(quán)威,除了承擔(dān)地方水利組織工作外,還負(fù)責(zé)稅收等官方職責(zé);再次,地方社會(huì)人們之間能夠較為默契地分享水利使用中的倫理,即公平觀念———將水利看作是“公共財(cái)富”,人們力圖將水資源轉(zhuǎn)化為自己的私人財(cái)富,同時(shí)也能夠遵守習(xí)慣法中的共同約定,投入勞力,維護(hù)水利。農(nóng)業(yè)社會(huì)的慣習(xí)化倫理,成為水利組織有序運(yùn)行最為有力保障。最后,水利也成為了整個(gè)國(guó)家體系與地方社會(huì)發(fā)生關(guān)系的關(guān)節(jié)點(diǎn),國(guó)家通過對(duì)地方水利組織的合法性認(rèn)定,并且憑借官方權(quán)威來強(qiáng)化水利的公共性與公平性而博得地方社會(huì)的道義支持③。
格爾茲在巴厘島的田野發(fā)現(xiàn)對(duì)我們理解農(nóng)業(yè)社會(huì)水利組織的政治邏輯具有概括性的啟發(fā):人們關(guān)注最基層灌溉單位是否“合理”,然后逐級(jí)向上感知,……“(從分水閘到一塊塊的水田)在這一體系的每一個(gè)層次上,從最基本的層次到最綜合的層次,存在著一種由分水閘與水渠確定的單位之間的互補(bǔ)性對(duì)立。在整個(gè)體系中,眾多具有結(jié)構(gòu)性對(duì)等意義的單位共同構(gòu)建了一座逐級(jí)遞升的用水權(quán)(管理)金字塔”[27]。
三、當(dāng)代水利———農(nóng)業(yè)水利向生態(tài)水利的轉(zhuǎn)型
從清代的晉中水利轉(zhuǎn)到當(dāng)代———我所面對(duì)的內(nèi)蒙古東部農(nóng)業(yè)區(qū),歷史恰似流動(dòng)著的水一樣,帶走了往昔那一幕幕因水利而被凝聚的世家大族、因水利而結(jié)下的血海深仇、因水利而祭起的水母、龍王、因水利而篆刻下的碑刻銘文
首先,與擁有發(fā)達(dá)水利文化的傳統(tǒng)社會(huì)最大不同的是,當(dāng)今農(nóng)村農(nóng)業(yè)收入占農(nóng)戶人均收入比重大大下降。就我調(diào)查的福鎮(zhèn),政府公布的2003年人均年收入為1090元,我所在大隊(duì)當(dāng)?shù)厝司恋孛娣e為1·1畝,以種植玉米為主,當(dāng)年玉米畝產(chǎn)約500-600公斤,當(dāng)年玉米8月中旬收購(gòu)價(jià)為0·38元,那么,人均農(nóng)業(yè)收入最高為228元,占人均年收入比重約為12%,而占了人均收入比重百分之88%的部分則來自于非農(nóng)業(yè)收入,即外出打工收入。在人均農(nóng)業(yè)收入的228元中,我并沒有計(jì)算生產(chǎn)投入的費(fèi)用。當(dāng)年春耕時(shí)期,我房東老兩口耕種了三畝多的玉米地,花費(fèi)灌溉費(fèi)用64元。隨著土地沙化日益嚴(yán)重,不可能發(fā)展經(jīng)濟(jì)作物種植,當(dāng)?shù)厝嗽缇鸵庾R(shí)到,依賴土地沒什么出路,所以不僅年輕人,甚至60多歲的老漢,只要身體沒什么大毛病的,都外出打工賺錢。人們對(duì)土地和水的關(guān)注越來越淡薄,很多人認(rèn)為,種地只是在盡一點(diǎn)農(nóng)民的本分,不指望著靠莊稼掙錢。同時(shí),當(dāng)?shù)氐霓r(nóng)產(chǎn)品貨幣轉(zhuǎn)換率也越來越低,每年種下的小麥幾乎全部留作自己食用,玉米磨成粉以后,則與北部山區(qū)的農(nóng)民換土豆粉和口蘑,糧食的商品價(jià)值很低。[31]
農(nóng)民早已經(jīng)被卷入市場(chǎng)化經(jīng)濟(jì),依賴貨幣生存,但是土地卻越來越不能滿足農(nóng)民的貨幣需求,所以農(nóng)民們不可能象傳統(tǒng)社會(huì)的農(nóng)民們那樣,將注意力和精力都投入到農(nóng)業(yè)生產(chǎn)中,相應(yīng)地,對(duì)于農(nóng)民而言,水利所體現(xiàn)出來的價(jià)值也越來越微弱,水利對(duì)地方社會(huì)的維系能力下降。一方面是人才問題,眾所周知,當(dāng)今農(nóng)村人才外流現(xiàn)象十分嚴(yán)重,即使是在村的能人,他的精力基本不放在農(nóng)田水利方面。所以如必然活躍在傳統(tǒng)水利社會(huì)中的地方精英———渠長(zhǎng)、水甲、渠斗,現(xiàn)在則很難找尋。形成不了“社會(huì)分層”的社區(qū),農(nóng)民呈現(xiàn)“原子化”傾向,組織過程要付出極大的成本,這是許多“缺乏分層與缺失記憶的低關(guān)聯(lián)社會(huì)村莊”無法成立地方水利自治組織的普遍困境[32];另一方面,任何組織系統(tǒng)的維系都會(huì)消耗成本,對(duì)于鄉(xiāng)土社會(huì)來說,成本包含了兩個(gè)層面上的意義,除了錢———這一硬性成本以外,還有柔性成本,如人際溝通,包括說服、監(jiān)督、沖突、排斥、整合等。在農(nóng)民心里,“掂量”該不該行動(dòng),所包含的考量,柔性成本的部分要遠(yuǎn)遠(yuǎn)大于硬性成本,在當(dāng)?shù)厝说男睦锾炱缴?10元+合作成本>50元+零合作成本。表述在人們口中的說法是“懶得生操那分心”。對(duì)于北方旱地農(nóng)村社會(huì),農(nóng)民選擇不合作是出于理性的選擇,選擇荒疏水利也是理性的選擇。
伴隨著農(nóng)民對(duì)水利建設(shè)日益冷漠的是農(nóng)民對(duì)社區(qū)依附性減弱,基層組織參與度降低,農(nóng)村基層社區(qū)不再是一個(gè)能夠吸引能人、資金、道義和國(guó)家關(guān)注的焦點(diǎn),就社會(huì)資本吸引能力而言,當(dāng)今農(nóng)村基層組織被邊緣化,成為消散優(yōu)勢(shì)資源的弱勢(shì)組織。與歷史上的地方水利文化相比,如今的市場(chǎng)化、分散化和低利潤(rùn)化的農(nóng)業(yè)社會(huì)已經(jīng)將再現(xiàn)往昔的豐富強(qiáng)大的水利文化了,歷史終成為歷史。目送歷史的背影遠(yuǎn)去,我們發(fā)現(xiàn),當(dāng)今的農(nóng)村基層水利建設(shè)思路不能局限于對(duì)過去的想象中,尋找切合實(shí)際狀況的水利建設(shè)路徑,才是解決問題之道。就北方旱地農(nóng)村,尤其是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脆弱的地區(qū)而言,應(yīng)該將水利建設(shè)從農(nóng)田型水利轉(zhuǎn)變?yōu)樯鷳B(tài)型水利,即放棄水利是農(nóng)民生計(jì)手段的觀念,建立起水利是生態(tài)資源的觀念。放棄前者,則水利市場(chǎng)化之路不通,既然在當(dāng)?shù)?農(nóng)業(yè)利潤(rùn)率非常低,農(nóng)民就不應(yīng)該再向市場(chǎng)付費(fèi),或者說,用水泵抽取地下水賣給農(nóng)民種莊稼用,賣水戶得到的錢,和農(nóng)民收獲糧食得到的錢,都沒有因水資源浪費(fèi)而造成的損失大,所以,放任市場(chǎng)化經(jīng)營(yíng)水利,是造成環(huán)境惡化的主要因素,市場(chǎng)化的利益主體應(yīng)該從水利供給上退出;選擇后者,則將水利建設(shè)放在關(guān)系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的高度上,將政府引入到基層水利建設(shè)責(zé)任主體的位置上,為基層水資源的可持續(xù)使用提供有力保障。
水與其說對(duì)農(nóng)民的生計(jì)之本,不如說是國(guó)家的生態(tài)之盾,水對(duì)于國(guó)家的生態(tài)環(huán)境的意義要遠(yuǎn)遠(yuǎn)高于增加農(nóng)業(yè)產(chǎn)出量的價(jià)值。就生態(tài)層面上來講,國(guó)家是有義務(wù)承擔(dān)起建設(shè)節(jié)水生態(tài)保護(hù)型水利工程,國(guó)家應(yīng)該成為北方干旱半沙化地區(qū)水利供給的責(zé)任主體。在北方旱地地區(qū),用水的主題不再是傳統(tǒng)意義上的生存與發(fā)展,而是現(xiàn)代意義上的生態(tài)與可持續(xù)發(fā)展,在這個(gè)意義上,傳統(tǒng)的水利是造福一地,而現(xiàn)代的水利是關(guān)乎一方,這一方代表的是上萬平方公里的環(huán)境資源。例如,省市一級(jí)政府要積極介入到基層水利的使用和建設(shè)中,設(shè)立基層水利管理機(jī)構(gòu),開發(fā)小農(nóng)田水利項(xiàng)目,建立引水、蓄水井窖,做到“節(jié)水、攔蓄、補(bǔ)源”。這一效果的達(dá)成需要合法化的組織保障,在目前的分散型用水模式下,浪費(fèi)無法遏制。所以,國(guó)家權(quán)力要保證下達(dá)到基層,將農(nóng)戶納入到集體化的用水組織中,抑止分散的個(gè)體用水造成的資源浪費(fèi)。